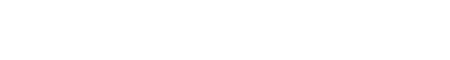大千世界,如若与某个地方发生那么一点瓜葛,印上一串足迹,真的得依靠一份缘分。上半年时,一伙朋友去四都、白虎堂采风,因故没能随行,就想恐怕再无机会结识这两地方了。何况这两个地方又一个在东,一个在西,远离都市,都隐藏在群山沟里,要我抽出时间,分开身子,找着心情,自己独个远足,我是连想也不曾想过。可也就机缘巧合,张家界爱心联盟组织的一次盛大空前的会员联谊活动,竟一下子将我推入白虎堂怀里,让我恍若坠入梦中。
其实这哪里是梦呢。我们长长的车队,载着多多的向往,一出小城,便向西,向西,风驰电掣!窗外的景色,那些田地、山头、村舍,那些家蓄、林木、溪流,你根本就瞧不出个啥模样,便“涮——” 地一下过去了,仿佛比我们那些颗怦怦跳动的心还要急迫。车在武陵源穿城而过,再驶往何方,对毫无方向感的我来说,已不重要,因为只那么一小会儿,我们竟已登“堂” 入“室”, 把白虎堂一下子塞得满满。
白虎堂村实在是太小,站在这个山头往那个山头传话,大概不需扯开喉咙作声斯力竭状。小也还有它小的妙处,那就是整个村舍的分布,零散是零散点,却皆被簇簇树木果蔬疏疏淡淡掩映着,营造出一种罕见的静谧。这种安静与生俱来,原汁原味,纯天然也,与武陵源的山水风景虽同属一脉,却比武陵源更幽、更静、更野!
白虎堂尚未开发。她的山水树木千奇百怪,不让景区,也就不被远方客人所识,却深受本地人亲近,简直就是自个家娱乐的天堂。一条山溪从山垭款款而出,不妖不艳,自自然然,似千尘不染的山姑从身旁低眉走过。那时你除了投以欣赏的目光,也许还会在心里大发感慨:这人世间怎么就还会有这么一条水流呢?
那溪水也太养眼。稀薄、清亮、欢畅,就是人常说洗衣能“亮色” 的那种。跌岩而下,积水成潭。那潭水又与薄流不同,颜色随阳光辐射角度而变化,或蓝或绿,或深或浅,变幻无穷。在这盛夏,可喜坏了一帮村童,他们才不顾忌旁人的眼光,赤条条的,扎“猛子”,使“狗爬”,逮“排手”;甚至登上小山腰,腾空一跃,跌入潭里,其架势、勇气、豪气,绝不逊色那些奥运跳水名将,可把一潭幽灵搅乐了,也把一众如我旁观者之心搅活了!
心如止水、旁若无人的自有人在。他们三个一伙,五个一群,席石而坐,就着烧烤,喝酒、扯谈,尽情享受着山谷蕴藏的轻风,能上大价的空气,悠哉乐哉。啧啧,这情形我们几时见过?又何时拥有过?我们是再也呆不住了,我们向峡谷腹地奔去。
最急迫的永远是孩子们。“妈妈,我在哪儿换泳衣啊?”“爸爸,那水凉不凉啊?”五六个金童玉女问来跑去,两三只小狗撒着欢儿跟来追去。能吃,是人最基本的需求;吃好,不在于环境;但要吃出韵味,吃出精气来,则是可遇不可求了。深谙此道的大人们,忙于搬石围炉,架网升火,回答孩子们的问题总是三言两语。一溪的水花,一溪的欢笑,一溪的佳画。
我把目光从溪谷里悄悄地收回来,不经意地投向对面山头,只见一棵古松郁郁苍苍,伫立危岩之巅,繁枝舒展。它之顶空,天蓝如洗,云朵轻移,山鹰飞翔。咯咯咯,哈哈哈,一串格外响亮的笑声入耳,引我迅速遂声回目望去,只见一位年轻的母亲,牵引着她年少的女儿,溯溪狂奔!水花四溅,晶莹如玉;长发飘飘,如练如瀑;笑声清脆,似歌似铃。好一幅母女山野戏水图啊!
一匹红马响着铃铛从山谷深处而来,背上驮着殷实的赶马人的喜悦。一群不讲究年龄的男女从山外涌来,在溪塔上扎堆狂欢,似乎忘记了往日的吃相。这些之前彼此还是陌生人的闯“堂” 者,竟在这一刻消除神密的面纱,融为一体,严然一大家子,在共庆团聚而豪饮!
我感动,却无话可说。硬要说,我只对白虎堂说,对不起,我们吵着你了,请原谅我们的擅自闯入。
可是,城市里高楼林立,人群如蚁,看着的是繁杂的什物,听着的是烦杂的声音,闻着的又是水泥那沉闷的气息。白虎堂,你说我们不在你这儿疯狂一回,又能去哪儿拾捡童年的情趣?又在何处寻觅一份轻松的心情,去工作去生活,去与沉重的人生抗争?
白虎堂,我不说再见,我们还会再来,尽管你的名字听起来虎气森森!